|
|
您好!注册登陆后会显示大图和更精彩内容!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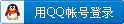
×
温适故里是梓桐
发布|余昌顺
除了王阜,梓桐是淳安最为独立的空间了。与其它乡域之间都保有地理隔离,不是少有几个村地处其它流域,它基本是一个密封的世界,尤其是在过去。梓桐源就是梓桐源,不一样的地理空间,梓桐源在杜井也就是现在的集镇这里分了岔,变成了两个源一个主源一个辅源,主源仍叫梓桐源,辅源叫黄家源。整个梓桐基本就是这个面积与这个形状,但处在山顶岙地的富石村是个例外,它的水是往界首流的。还有个例外是从黄家源翻过枫岭到了龙源的源头地带,这里目前有两个行政村也属于梓桐,而龙源是姜家的一条主要流域。整个流域的溪流基本是从西往东进入千岛湖,流出域外。而龙源是从北到南流的,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像在黄家源的屁股上加了一竖笔,所以从原来的卧着的“丫”形变成了一个耕田的“犁状”。不知这里有没有什么宿命的意义。
凡密封的世界都有出口,梓桐源的出口,就在一个叫梓桐口的地方。梓桐口及其上游十几里路的广大空间的多个村庄,随着千岛湖的形成都已淹入湖底。昔日的村庄现今已成碎片,每个村都已支解成好几个村散落在浙赣两省好几个县。留在梓桐的部分,都成为一些小小的后靠村落或组合村庄。
梓桐口这个重要的地域,如今也叫梓桐口。目前只是一片被人们称为“最美峡湾”的广大水域,口子的样态因千岛湖的形成而有了变化,但狭窄的空间仍然如故。然而昔日的口子,才是真正的口子,梓桐溪从这里入新安江,新安江畔还有这么个神秘的地方。
洞穴桑梓的温情
在今上埠岛这个地方,就是过去的狭义的梓桐口所在,它在1959年前就是一座疑似独立的山且横卧在梓桐源的出口处,它的南边是梓桐溪的口子。它的北边是一个小小的山口,上埠山与其北面的山有着似连非连的撕扯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这座上埠山并非完全是独立的,人们进出梓桐源,得爬一个低低的岭,这里就像一个门。而南边梓桐溪出口的地方是峡谷是悬崖峭壁,所以进出只能走这个“门”或者说走一个像门一样的岭。祖先把这个岭给凿了,成了真正的“门”,顶上砌上石头,两边是石头,看起来,像个堡垒,当然更像是一座城门。这座城门上还建有一座寺庙。当地人把整个这个布局称其为洞,确实像洞,而过了这个“洞口”里面的空间更像是“洞”。洞往往有着巨大空间、安全、温暖等延伸义,所以,梓桐源因为这个洞的形态,而完全不同、完全独具个性。
这个如洞一样的门叫:梓洞。没有称门,而称洞,我想梓桐的祖先在命名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进出如门的小概念,而是整盘考虑了梓桐这源里的空间地形,把它当作大梓桐来考虑。所以,人们都说梓桐这名称是由梓洞而来的。梓洞引伸到梓桐说来也合理,把一个156平方公里的区域简单叫成“洞”,也并不雅。而在梓桐的范畴里过去是否有许多桐树,不得而知,但桐树在淳安也是很普遍的,过去在淳安有这么一句俗语:开山不种桐,到老都守穷。所以,这里也一定有不少桐树。最为关键的是“梓”与“桐”这两个字一个是故里的意思,一个是陪着故里的景致的意思。况且这两个字在古诗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所以,一看到它们就有高贵、典雅之感,有风雅、音韵的古风,进而有温情桑梓的微风和煦。在当今还有桐坑源、桐坑口、桐岭脚这样叫桐的村庄,还有桐坑坞、桐岭这样带桐的地名。而桐坑源既是一个村名,也是一条小源的名称。翻过这条源就到了另一个与梓桐源垂直的龙源,而这个岭就叫桐岭,那边岭脚的村叫桐岭脚。我觉得这一堆有桐的地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何以叫梓桐的原由。
从梓洞到梓桐,似乎也顺理成章,但为何叫梓洞呢?是那座叫上埠的山上从前有许多梓树又有梓喻故里?还是纯粹取“梓喻故里”叫梓桐呢?
练溪村目前几乎是梓桐源最外面的一个村了,这个村是移民后靠村,来自好几个母村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千岛湖形成后的好长时间里,这里是梓桐的一个桥头堡,因为它就是梓桐码头。与练溪相仿佛的是西湖村,是练溪的邻村,与它隔水相望。这个西湖村其实是8个小小自然村组成的,这8个村有一半都叫坞,比如:下坑坞、上坑坞、密溪坞、牛栏坞等等。这些坞从前都不是村庄,全都是梓洞口以上几村的部分移民后靠村。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村庄藏进了一个浅浅的坞内:村口一大水,村内一小涧。大水就是千岛湖,小涧就是后山上的一泓泓小水,这小水维系着村民的饮用。它们几乎都依偎着村后的两座重叠的山:鱼口尖与青山尖。背后的青山高高的,山顶常常云雾缭绕流岚氤氲。浙江理工大学教授严渊博士说,这些村背后的山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凤凰。这一堆小山村,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是被遗忘的角落,前几年梓桐与千(岛湖)汾(口)公路的连线工程从它们村前而过,这里又成了梓桐的另一大门。如今它们朝着东北方向,村庄仍旧低调,但无法不被正视,当看到它们我总感到还有丝丝的羞涩感。每到秋冬季节,村前峡湾里的满山红叶染红了天空下曾经的青山。一边是声音的宁静,一边是色彩的热烈,它们所形成的张力,让人无法不激动,甚至很难调动到平衡状态。
2019年9月1日,我们在练溪村口的一个长廊里与几位老人聊了关于梓桐口与梓洞的一些事情。91岁的余花子仍然耳聪目明,看不出超高龄的样子。吐字清晰、目光有神、声音洪亮,他说:“从前,抓壮丁的人都不敢进来,走到梓洞口一看这阵势都退了。”所以,自古以来梓桐都是和平景象,洞内的梓桐源没什么暴戾的情况。
“梓洞的上头有座庙,”胡永胜也81岁了,他接着余花子的话说,“在这庙里常年有人给过路行人烧水。”出了梓洞口就是新安江了,沿着新安江往上到威坪往下到贺城,这两个都是新安江边的古镇,一个是县城,一个是曾经当过县城。到威坪35里,到贺城45里。在梓洞口,就要面对大江了,就要走出温暖的故乡了。梓桐人就要闯码头去了,来自新安江广阔江面的风,总在梓洞口徘徊,经过梓洞钻进梓桐源的风其实并不多。无论是狂风、大风还是小风微风都被梓洞过虑过,留给梓桐人民的感受常常不大。他们生活在一个安全、温暖又相对舒适的地理空间。
这样的空间,应该是和平和煦的,应该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但凡事都有例外,谁也想不到中国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女领袖陈硕真就出在梓桐源。她在公元653年率众起义,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一个33岁的年轻女子居然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大事件,让所有的中华儿女都目瞪口呆。那时,我们的大唐才过了35年,应该是初唐“蜜月”期还没完全结束,至少还没有到一个王朝的腐烂期,所以,她的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但有一个人可能不这样认为,在陈硕真酝酿起义的紧锣密鼓期,武则天也在紧锣密鼓地与皇帝李治抓住每一次宠幸的机会缠绵。努力制造皇子,陈硕真起义失败的第二年,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出生。她利用长女的夭折,在夺取权力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陈硕真的刀光剑影远远不是武则天的娇媚中的计谋,但我始终坚信一点陈硕真的起义一定为武则天的思想形成或者说野心成型给予了巨大的催化作用,使她的“女权思想”进一步坚定:女人也可做皇帝,民间女子都有此想法。剪伯赞为陈硕真下过这个定义:中国第一个称帝的农民起义女领袖。作为同龄人,陈硕真与武则天除了同在大唐的蓝天下外还有没有什么交集呢?
她俩在坊间有一个《俩女皇》的传说,说她们在感业寺中有交集,公元650年,同在感业寺。陈硕真还为武则天打包过不平,有纨绔子弟调戏武则天,武艺高强的陈出手相救。我对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充满着怀疑,梓桐源与京城长安太远了。而陈硕真所在的村田庄里是一个很小的村,这个处在淳安腹地的小山村很难与京城有联系。千岛湖形成后,这个村被淹了,田庄里已经牵到江西吉安井冈山脚的凤林湾村去了。村庄还是那么小,但仍保留着坟墓不立碑的习俗。坟墓不立碑也是由陈硕真引起的,当年陈被官府镇压后村里人拉回来了尸体,为了不让人找到村里的坟墓全不立碑。
梓桐镇的退休文化干部叶福生说,听淳安县文化馆的已故老馆员王召里介绍,在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书记载:说到宋江的梁山造反就二十多个字,而说到陈硕真有两页多纸。但事实上是《水浒传》有百万字留传千古,而陈硕真无人书写,记得她的人也寥若星晨。叶福生所发出的遗憾语气让人感动,但历史中有多少该记住的而未记住的呢?我们在叶家庄村叶福生家里喝着浓浓的茶,听他述说这一切。他还带我到村边,向北望远处的山,说那就是丹凤朝阳。在“凤嘴上”从前是一个古墓,盗墓者在打开这个墓穴时,飞出了一只受了伤的凤,人们把这受伤的凤喻为陈硕真。这样的传说反映出朴素的思想:失败是注定的。那里的地理元素也没有配合陈硕真的起义。
这里的地理相对是温婉的,山形地貌鲜有嶙峋险恶之态,不太长得出暴戾的气氛。在这样空间里生活的人们勤劳、温和,没有厉害的抗争形象,而且梓桐是一个旱地偏多的地方。旱地远远多过水田,一般以旱地为主要生产空间的地方,人们一定会陪上加倍的勤劳,才可以生产出满足繁衍的粮食所需。所以,这个地方出了个陈硕真是严重不符的。甚至因为陈,现代人说梓桐是个出美女的地方,这当然一定是美丽的喻言。但我在想,现在的梓桐人与陈硕真时代的梓桐人的人文性格完全起了变化,是否是陈硕真被镇压之后大家有意的收缩呢?
姜宅村的姜伟大,给我说起另一种人们的经历。姜宅基本处在龙源的源头,过去进出也大多走威坪。村里人从桐岭脚起步翻过桐岭到桐坑源再到桐坑口,然后顺流而下到结蒙,从这里开始往赋置岭走,翻过赋置岭进入鸠坑的赋置源,走出源口过新安江到古威坪。从姜宅走到威坪要35里多路,得翻两个岭,从前都是这么走的。后来千岛湖形成了,他们也是这么走的,因为赋置源口成了一个重要的码头,那里一带物资的进出还是要走这条路。
姜伟大说:“我们处在一条源的末尾,所谓旱地就是山场,不可能像传说那么多粮”。这说明村里人厚道、温和,不懂得自我收缩保护自己。所以在从前姜宅村里就觉得税赋很重,但也默默接受,把这种不合理编成一个笑话,一说了之。
一走三十五里路,
一担粮食挑到哭,
买三担归;
卖一担去。
常过赋置岭并不是只有姜宅村他们要走的路,而几乎是中桐以内所有梓桐人都要走的路,这条路是“车水马龙”的“大道”,虽然它只有1.5米宽,虽然它要翻越一座岭。见证赋置岭热闹与繁华的是张素珠,她出生在岭上,16岁才随父母下山到了石岭村居住。今年79岁的张素珠说:“我们家在赋置岭上住了10代,两百多年。”
赋置岭的繁华造就了张家的日月,但没有造就张家的兴旺。按张素珠的说法就是“基本是代代单传,偶有不单传也是留一位在岭上。”到了张素珠这代就她一个女儿,没有其他兄弟。几百年的风霜雪露成就的沧桑,都落在了张家的屋顶,积厚了瓦片上的风尘,就这样她家成了岭上的独特风景。结蒙村的徐爱仁提供了一种说法,他说赋置岭上的张家给大家提供帮助,父老乡亲都记在心上,所以,到了割稻的季节,张家只要挑着担子来,在谁家田里拿点谷子都不会有人反对。因为,张家在赋置岭上两百年为大家做了多少好事呢?数也数不清。
赋置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是梓桐人民通往古威坪的主要通道,梓桐的物资进入基本都依赖这个通道。出去的木头等大宗物资经新安江运往杭州等下游,其它日用品从威坪采购进来。这样的流通就需要一个保证,后来在结蒙村就成立了义渡会,统揽物资的进出。义渡会还有一个场所,就是一幢房子。“那屋子到1960年才拆除,”徐爱仁提高嗓门,“所以说,赋置岭是梓桐源里的‘通衢’。”
张素珠没有认可拿大家粮食这一说法,她说岭上有土地的,可以自给自足,这么一小家人填饱肚子完全没有问题。我想无论徐爱仁的说法是否符合事实,赋置岭上张家的存在本身就能说明一个问题,梓桐人的仁与义,爱与温暖。是这些组成的人间岁月,温暖了赋置岭上的山路,润泽了梓桐源的沟沟坑坑。张家两百年是为大家烧水泡茶的两百年,是看着通道熙熙攘攘的两百年。“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水缸,每天都泡满茶,”张素珠说,“有些时候也提供人家吃饭。”当然吃饭是少数,不是不得已一般客人不会提出来。有些时候也有提出住宿的,当然不是万不得已的非常情况没有人提出来要住宿,所以,他们张家主要是义务给大家提供茶水。张家为大家提供喝水,过往客人给张家带来了热闹与风情风景,但几百年如一日也不容易。
张素珠在那儿出生,从小目睹的是这样繁华的情景,所以她也不觉得寂寞。她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几分沉入其间回到从前,她说有两栋土墙屋一直一横,横的朝东。屋前屋则有七棵古柏树,这些树是她记忆里最清晰的影像。树上随着季节的不同,一天时辰的不同会有不同的鸟栖息。树下是各种路人席地而坐,错落有致,有空手过路人,有迎新的队伍,但大多数都是有担子的。人们把担子卸下来,有的把担子依偎在两株相邻的柏树间。这就是她童年里的主要场景。她10岁开始到山下石岭村来读书,有时她会与那些挑担子的一起走路,会在他们中间穿梭。
她说:那个岭上已经十多年没去过了,现在已经无人过岭,这个岭只能存在于我们这些老人的记忆与想象里,不知上面是什么样子。当然,自己曾经住过的屋基一定还是能认得的。
寺庙佛殿的注释
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是明清交接期,世事变更所扬起的尘埃还没有完全落定,在这个飞尘慢慢趋定的过程中自然会有很多变故。在淳(安)遂(安)交接处的龙源源头区域,也正经历着尘埃落定的过程。这过程充满着诡谲,说遂安两位划界官的大意丢了龙源的源头三村。
龙源流域属姜家镇管辖,以前除了源头三村外整个流域几乎就是龙泉乡一个乡域的地方,1992年并到姜家镇了。从前这里属遂安地界。当然龙源流域的最里面三个村墩头、江家、姜宅(那时还没有桐岭脚村,此村是姜宅人住进去的),属遂安管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至今这三个村还讲着与姜家相同的方言。但事实上,它们归淳安管辖,淳安跨流域把龙源三个村收编了,所以梓桐镇得翻过枫岭来管理这片15.7平方公里的区域,这只占全镇的十分之一。如此便有了传奇般的故事,故事并不复杂。
说明清过渡期,淳遂两县对不甚清晰的地方进行重新划界,当时遂安派出的两个划界官在源头的花果庵里睡大觉,等他们醒来,事情已经敲定。后打官司到严州府,知府也无力改变,就把花果庵里的几尊菩萨判给了遂安。事后留下了一个千古笑话:争得菩萨九尊,丢了龙源三村。
姜伟大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是想告诉我这个龙源的源头山上有一个花果庵,很有名的,在鹰峰的西边。以上的故事只是旁逸出来的笑料。我说去那里远吗?可以去下吗?姜伟大说,恐怕你们没时间。当时是在姜宅村的村委大楼,他说去哪里得走另一条支源,往外走一里多点路然后西拐进去。到源头还要爬山,因为它坐落在一个多流域共享的坪里。
花果庵其实是那座山的骄傲,那座山确实值得骄傲,往小里说那块坪也是四个涧流的发源地,其中西边一条就是朱熹在《读书有感》中提到的郭村源头村那条,它的部分水流入半亩方塘,成为朱熹造诗的上好材料:为有源头活水来。庵堂旁边还有一株古银杏树,已经差不多1400年,苍天的银杏几乎统治着这座山与山上的庵堂。现在庵堂还有遗址在,当然那株银杏也成了遗址的地标之一。庵堂里的菩萨判给遂安管后,姜家的郭村那边有个财主也确实对菩萨进行过维修。但那座庙所坐落的地方,仍然属于姜宅村,如果说那座庙与庙里的菩萨归遂安管,那也是一块飞地。可能,那时庙的作用比较神圣,然而这样的行为只为那个笑话增添了更多的佐料。
花果庵毁于一把大火,1935年因地下共产党员把庵堂做为他们秘密聚会地点,国民党的保长派人放了把大火。庙就这样毁了,没了这个庙好多故事也开始流浪了。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关于这个庙宇的缕缕支杆,有人说名山好山都被庙宇占了,反过来庙宇又能增添山的名气。姜伟大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那一带名气的式微感到恐慌,所以他耿耿于怀。这块多流域出发点的三角地带,目前已人迹罕至,作为山可能更为归于本真。但作为名山的它只能与花果庵的传说一并存在,当然那棵古银杏还在成长,它见证了花果庵的兴衰存亡,也保守着它的秘密。它会成为花果庵的另一个标记,存在着。希望它与这个古老的树种一样,能永生下去,从这个角度说人迹罕至肯定是好事,能对它生命构成威胁的肯定是人类。孤寂会让它更为自由酣畅地成长,它只会与它树抢夺蓝天,但它早已赢得了先机。
姜伟大的失落不是古银杏的寂寞!
在梓桐几乎每个村都有关于庙、殿、庵的记载与传说,它们的遗址遍布在梓桐大地的角角落落,这些并不起眼但总在民间滋润着什么,使这域大地变得温和,使种粮的山地遍布山山岭岭。面对土地拮据时并没有选择暴戾,而是选择另一种形式,自我精神内解,尤其是陈硕真之后。
翻过枫岭就是黄家源了,这个源不是梓桐的主源,但比起主源来与下游之间更直,基本成一直线。常常会产生错觉,这就是梓桐的主源空间。但这空间不大,溪流自然也不大。流域平坦,旱地不少,梓桐出产玉米与番薯,是不是与旱地、山地多有关?梓桐玉米粿成为一大民间特色主食,番薯衍生出的番薯粉、粉丝、番薯干都比较有名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一个地域种什么庄稼一定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里选择了玉米、番薯等旱粮一定有其原因,旱地是无水的地,无水的地有两种,一种是天然的相对较陡的坡地离水很远,一种是完全可以改成梯田但没有足够的水源。在梓桐似乎两种情况都有,像梓桐正源的源头村石门塘,它的源头地域是一块空旷的平地,但这里只能当旱地种不可能有水,因为是源头,是水的产生处。这个村的少水还有一个验证,80岁的姜产传告诉我们村里旱的年景多,一般到了夏天后,就进入了枯水期。从前,枯水期饮用水都很困难,每天一大早就在门口的小坑里排队挑水,日子一久这成为村里的一景。每年大年三十,都要把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生怕到了大年初一水不够用,再去挑水不利市。同样的源头村桐岭脚,有五个涧水向村里流,但到了8月底9月初大多已断流,剩下的是点点水滴在石头上渗透着。
打开梓桐地图标示流域的绿色曲线也很多,围着梓桐溪主流像鱼刺一样在两边伸展,但这些支流普遍较短,没有大水的地理条件。所有的支流都不长也不大,在秋季基本都处在断流的状态,除了桐坑源还有一点点水外其它的都已干涸。桐坑源有一段溪在村中过,而这段溪床基本是巨型石头,水在石头上流过形成各种形状煞是好看,像人工做起来的水泥景观,小小水流打上面过,如同水枧、水槽。梓桐正源的源头有两水交汇,一是石门塘来水,一是银川坞来水,在一个叫杨家屏的地方交汇,因一屏山似墙壁,两水在屏下成东西对冲之势,这里就留下一个深深的潭,2019年9月1日看到的此潭似乎也是深深的,由于有了蓝藻深的感觉更加充分,但石门塘与银川坞的来水都在流入此潭前就已断流,躲到砂砾之下去了。
梓桐山塘水库也不多,全镇总共4座,说明水源并不丰润。其中有一座就在富坡村,叫碓坞水库。这个碓坞的水是从南往北流的,南边是与界首的界山,像墙壁,所以这样的山没有纵深,自然碓坞这个支流不可能长,水源也不会太多。过去估计富坡就是靠这个水库灌溉农田的,富坡缺水是比较有名的,因为这里还有着传说故事。富坡与其下游的杏坡两个村相距两里多路,但却有着不同的对水的体验,现在它们已并为一个行政村叫:杏富。这村名很让人想起“幸福”。杏坡村的胡富财在讲起两村两则有关水的故事时有点眉飞色舞,觉得杏坡人不仅比富坡人幸运。
关于富坡缺水的传说其实与威坪五都、小五都的稠林与杨家两村缺水的原因一模一样,神仙化装成叫化子路过富坡,见富坡人在车水叫化子要经过。车水人说:你在水车下钻过去吧。叫化子钻了过去却留下了一句话:人打下面过,水打地下流。从此富坡就十年九旱了,水成了他们永远的痛。而杏坡人就比富坡人幸运得多,当然这幸运是用“好人”的作为换来的。同样的这个神仙在路过杏坡时,问杏坡人讨水喝,杏坡人就去村头的一个仙人洞里去接那滴滴嗒嗒的水给叫化子神仙喝。神仙问:为何要跑那里去接水呀,那里水也不大呀。杏坡人说:我们没水,缺水喝哟。神仙随手捡起一个拄棒一戳:这不是水呀,这不是水呀。拄棒所戳之处,都有泉水喷涌。从此后,杏坡人就不缺水,即便到了枯水期,由于有地下水,也没有富坡这么干旱。胡富财把这两个故事当一个故事讲,味道就来了。他说:“这就是活水名堂”。
少水是梓桐的艰难之一,这些来自自然的困难总能投射到某些可能中和它的事件中去,那便是寺院佛事。这种和缓内省的与困难作斗争的方式,一直传承千年,使这块大地上的每个地方都布满寺庙佛殿。有大有小有久有短,在梓桐的每个村庄里都有寺庙的传说遗址,在民间有着深深的流传,佛事都与平安、兴旺、健康、吉祥相联系。杏坡也有一个很有名气的“道山庵”,庵坐落在水的南边,一垄从次山巅逼过来的急促山在溪边煞尾,留下了半个球体的样子,三边都是光滑的悬崖。“道山庵”就在球形的顶部,从里商嫁过来的莫冬花说:“这个道山庵过去很热闹,香客如云,年轻时我也是常客,文革后期被毁了。”现在已经无寺的这座山看上去还是很有气势,石壁上密密的阔叶布满期间,使巍峨向中间过度,产生峻峭的气概,使整座山从那壁山中分辨出来。
与“道山庵”相对应的有座不大的山,它是一座孤立的山,形状如一艘船覆转过来,村里人称其为匍船形。这座山十分的吉利,与其形体小相反,这是一座非常“大”的“小山”。我走上山,74岁的胡金澄正在打山核桃。“珪公的坟就在这山上,”他指了指东侧的那座移动公司的铁塔,“就在那塔的下方。”
他说的“珪公”就是梓桐胡氏的祖先,到此定居已经七百年了。胡氏在梓桐很有地位,过去有胡半源的称谓。这么兴旺的姓氏,其祖先的“古冢”在后代心目中其地位自然不一般。
梓桐最有名气的一座寺庙,应该是尹山庵了。尹山庵自然在尹山村,尹山庵由尹山得名,“尹山”这个村名因尹山庵而“不朽”,但尹山村委所在地并不在尹山自然村,而是在十八殿坞。看看这个村名,就知道在梓桐其各村的小庙小殿之一斑。《淳安地名志》上有关此村的条目是这样的:
【十八殿坞】相传,古时该村有十八姓,每姓村民于村外附近建小殿,共十八座殿屋。后拆除全部小殿,合建大庙于村东。庙内塑有十八尊菩萨,以示十八氏祖。又因隅位山坞之中,故名。位于镇人民政府驻地西北9千米处。30户,90人,徐姓居多。聚落处笔架尖南麓山峦中。公坑溪绕村东南流。
这么小的村,而且还是徐姓居多,居然还有十八个姓,其先基本是一姓一户了。十八姓氏建了十八个殿,这就是梓桐的风气,殿不大名不响,但村村有、处处迹。我一直以为在淳安县文史委编纂的《淳安佛教》中,梓桐有关佛寺殿庙的记载一定很多,恰恰相反,仅有两处:姥山庵和尹山庵。说明这里的殿寺都很小,还处在民间对佛神菩萨的初级需求之中,面对自然所带来的困难还是要从内去求得平衡、心里求得平缓,那是陈硕真之后的平顺与驯服。
尹山庵必须要说一说,这个庵建于南宋淳熙七年至今已839年了。庵里供奉的是新安越国公汪华的第八子,汪俊修真化此,至今佛龛尚存。历史沉积下了许多诗文,尹山庵也就变得引人入胜了。尹山庵所坐落的尹山本身就有着自然景观禀赋,光凭山形地貌就能成景,加尹山庵,其叠加效应更为显著。在众多的游历赋诗者中有邻县的官人,有本身的知县,有朝庭的尚书,有本身的进士,不一而足。即使隔岭的邻村鸠坑的严村也把尹山庵当作其村的八景,其诗为证:
尹山古寺镇南屏,无复高僧解说铃。
犹幸梵钟鸣五夜,几人酣梦几人醒。
如今的尹山庵差不多是遗址了,主殿的屋子基本还有三面残墙,柱子也已不完整,尤其是靠近外面的柱子已是少胳膊短腿。梁与屋顶已成网状,风雨飘摇好多年,随时都有完全垮塌的可能。朝东的门口还有一往下入小广场的台阶还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样子,除个别有点残角、个别踩上去有点摇晃外,青石板还基本与原来相仿,只是枯萎的青苔与隙缝中的杂草在告诉人们这里已经鲜人到达。一些木料堆放在屋子的右边,屋后有挖过的大片痕迹。据说,这是在整修,那一带的民间自发凑钱对尹山庵经行一次彻底的维修,让昔日的千年古寺重发佛光,在民间可再发光芒。在从善从良的价值体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
尹山庵是这个庵名也是自然村名,这个村星星点点散落在次山巅,被人称其为天上人间。在庵的西边住着严氏兄弟三人,现在就严章红一人还守着老屋,一哥一弟都已进城,他不愿意去,所以三兄弟的房子基本是他守着。他说他老家是鸠坑严村的,爷爷手里住到这里来的。“住在这山上的都是犯了事的人,”他扛着嗓门说,“不是赌博躲债的,就是杀人放火的。”我问你爷爷是怎么来的,他说是赌博躲债逃来的。这样的人住在这山上,倒是消遥,离天近、离林近、离佛近了,离人远、离灾远了。我觉得这些人逃到此地总有种讽刺的意味,与追求良善、大慈大悲的佛为伍不觉得是十分不和谐吗?反过来说,给这帮走入歧途的人超度也是佛之功德。但严章红补了一句:“所以,我们这山上人都是不好管的,有那样的基因。”
“当然修整尹山庵,是不是就是趋同趋良趋善的机会呢?”严章红最后说。
89岁的余学胜是个例外,他4岁时被父母从郭村的黄坑坞卖到这庙里来。解放那年他19岁了,尹山庵散了,余学胜也返俗了。他就地安家娶媳妇,立业成门户。尹山庵的左侧有一株银杏,只有这古树才与寺庙的古老相匹配。过了这株树就是余学胜的家了。那天我没看到他,只看到了他的老婆叶艾玉,耳朵有些背的她,交流起来很吃力。半天才问出余学胜的名字来。一幢土墙屋,显得简单质朴,但门口玫瑰色的奥迪车显得很不般配。过来一会,一年轻女子携着一小孩过来了。这女子就是已经在城里生活的余学胜的孙女。这里已经是这条盘山公路的终点了。这奥迪与整座山的气质环境都不是很配,生出一种另类的力量出来。不配的还有两块石头,它们在余学胜房子的墙脚石上,已筑到墙里,显然这是来自尹山庵的某个构件。当时建屋时,余学胜不知是怎么想的,要把这两块石头筑到墙里去,是为了某种纪念?
比起尹山庵,大水坞殿就要单纯得多了。基本是村民乞求平安、风调雨顺的作用,还没完全上升到佛事的高度。简单有简单的好处,当它坐落的位置十分的好。殿后是梓桐的最高峰洋尖,殿里的菩萨可以直接看到远处的风景,这风景可不一般。
山岭村舍的水墨
当你以菩萨的姿势坐在大水坞殿里,透过门洞极目远方,就能看到奇异的景观。远处的山是另一个山脉,那是梓桐与界首的界山,姑且称其为富石山脉,因为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叫富石的村。这个山脉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像一堵挡土墙一样的山,特别是在梓桐看过去。挡土墙的那边就是界首,但界首那边有深深的源,而梓桐这边没有,在这边看起来就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塝一样,有高度没纵深。而且这山脉还一字排开很直,越过这边塝一样的山那边的水全是往界首流去。富石虽处在次山巅,但属于界首流域,水都是往那边流去,作为梓桐的村庄它孤悬在外。从大水坞殿里看到的风景就是富石村的一个大自然杰作:八面山。这八面山只有在这个位置看上去才特别有型,它们形成了一个巨型的砚台,神奇的是在大水坞口西边有座山恰恰似笔架,看过去前景是笔架,后景是砚台。
大自然给梓桐的山水造就了这么神奇的地理形态,不挥毫写字作画,怎么可以呢?这样的山势完全可以作为图腾:书画之乡的书画笔砚。
大水坞的溪流穿过的是并峰村,这个村是梓桐源里的一个节点。退休老师胡建新说起自己村里的地理满腔热情,一脸骄傲。他说他们村的地形地理十分出众,一两句话说不完。真正意义上的狮象把门,就是他们村这里。溪流在这里走了个横着的“S”,上游那个弯把水逼到了对面山崖下,溪在这里留下一个深深的潭。北边留出了广阔空间,就是并峰村及其村后的田地。南边的那座微曲形的低矮山形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狮,而随着溪从南往北弯过来后,从并峰屋后东边有座山的长长的缓缓的余脉逶迤而来,这个形状似象鼻,一直延伸到溪里。“现在象鼻不是很像了,好多人建房把垄起来如小岗一样的山地给削去建了房子,”胡老师满腔遗憾地说,“过去我们村是一个关卡,进出梓桐源必经之地,狮象把门,风水上乘。”
这个“象鼻”是形成并峰村的重要地理原因,有这个挡牢,上游的水再大都不可能冲毁这一大片地,而溪北这段超强的稳固,使这里形成一个高高的斜坡地,这坡地从并峰村里一直连绵到大水坞的出口处。这一个斜坡地现在由村庄、少量水田、大量旱地组成,这样的地形使村庄与大溪形成约20米的高度且这高度是不断上升。有趣的是因为有大水坞流出来的小溪穿村而过,一般情况下村民用水都在这条小溪里完成。这条涧溪很是不同,它是在一个高坡的高点线流过,而不是一般溪流都是在低洼处流过。同时,由于落差大,整条溪基本是冲阶而下,地面与溪床之间的高度也很高。这样的形状向上游沿伸,整条大水坞溪都是这样的落差,所流过的区域觉得是这条溪冲积出来的地,而土层无比的厚,所以溪水很容易断流。
大水坞这个小流域就成了一个不断台阶下降的流域,无论是在这个小源两山夹一沟的里面,还是走出这沟源之后。走出沟源之后是大片的土地,形成了高高的一直往村庄到大溪边的土坡,这广阔的地域就是并峰村的灵魂。胡建新老师一再强调,没有大水坞这个小源,就没有并峰这个村。当然没有象鼻这个龙岗的阻挡,也形成不了现在的这样的坡地。它与小源口子上的两座山,形成的地理要素成为村名的灵魂。
小源口子上是一对并立的形状十分相似的山,像一对卫兵也像一对人工按上去的三角形山的标准照。村名也由此而来,原先叫并坎村,并就代表这并排而立的大水坞口的两山,坎就是出了口子之后的广阔旱地,也就是土坎。多么贴切的一个地名,后来由于与方言谐音的原因,在行政村区域调整中,改成了并峰。虽然这并峰也不错,但我个人觉得并坎更为贴切。
在对面望这个“坎”,这一对并峰,以及整个洋尖下形成的大水坞样子,一定是几幅特别的画。村庄落在坎坡上、狮象对视、弯弯的溪、深深的潭……,这所有的一切都成画。
与这个“坎”相仿佛的是河山与后洲两村之间的地形,也是这样的落差明显的旱坡地,也有广阔的空间,也有一条从小源里冲下来的水。这水也容易被厚厚的土质所汲取,容易干涸,在9月初就已断流。这小小源水的后面也是一座高山竹尖山,小小的溪也是发源于这高山。这个坎与并峰村的坎不相上下,梓桐这样的坎不在少数,所以,它旱地多,旱粮丰。丰成习俗,丰成特产。这两个村名中,我总觉得能解读出某种地理的信息。河山与后洲,都与水有关,都与水形成的土地有关。在《淳安县地名志》中是这样说的:
【河山】此村北倚竹尖山,面对溪流,以前村后山之由名河山。
【后洲】明朝末年,徐祖昭公迁此,村前有平畈,后有山洲庙堂。建村于此山洲上,故名“后洲”。
我总以为此村名隐藏着神秘内容,即使这样的权威解释,我也觉得有密可破。像河山村,说前村后山,故叫河山。前村后山这样形状的村,在淳安总有百分之三四十吧,为何光此地叫这个村名。山河造化而出:像坎一样的旱地。后洲更为明显,洲一般是被水淘洗出来的。“后有山洲庙堂”里面有个山洲的概念,为何叫山洲,不就是那个小源水流出来的洲吗?
这竹山尖,是梓桐的三座高山之一,在民间有很高的知名度。常成为某种标志留在民间语言中,有一首说梓桐源的打油诗,虽是打油,但其间蕴含着很多内容。有风情、有俗语、有地理特色等等。诗云:
梓桐源里来客人, 小雨飘过茅庵桥; 一眼望到竹山尖, 心里想起倒汤瓶。
诗中说到的“倒汤瓶”就是次源头的一座山,那座山的山岗上有一处非常形象的象形石头,它像一个倒置的汤瓶,柄刚好倒置在山岗上,扣住了山岗。一眼望去就是一个汤瓶的柄,穿过柄眼,也是一块蓝天。山显出如此模样,当然让梓桐人津津乐道,大自然的神奇。过了这座山,就开始往尹山出发了。这座山如同尹山的半围墙,绕过它就到了尹山的视野。尹山是一座山的一部分,在一面缓缓的墙面上,长出了尹山的身姿,所以它是长在墙面的垄起的山,神奇就神奇在它垄起的样子是独一无二的。从山脚往上爬,最下面都分就是一个普通的山垄,登高三、五十米后,突然来了个悬崖形的地形。在这个地形中,都是些老树林,树间也是奇形怪状的石林与崖石,有质朴的石阶穿起来,让你觉得不知何时才走出头。当你内心刚有着继续长途跋涉的念头出现时,却已经走出头。一钻出如原始森林般的老柴林,完全换了空间换了气象。回头看,回头想,刚刚走过的那一片森林其实就像人工垒起来的塝,爬过了这个塝,就跃上了新一层。
这新一层,才是尹山的核心区域,才是真正的尹山。这个空间是次山巅,从山岗缓下来,刚刚在这个“塝”顶成边沿。缓出了大片大片的旱地,也就缓出了村庄尹山庵。尹山庵村稀稀拉拉,布置在这一方圆里。最高的房子,就差不多到了山岗,差不多到了石人岭的最高处。何为石人岭呢?因为在那个岗上,有一堆石人石马的奇形怪状的石头。从尹山庵遗址往石人石马看,有十分形象的石头形状,边上的两三幢民宅好像画上去一样:既有画面感又有远处感,既有青山绿树浓又有水墨粉画绸之形态。这种样子,刚好构成远方的边界距离,似乎过了这个距离就是绵延的远方了。
目光从石人岭那边往跟前撤的过程,横扫一遍那片空间,其实就是宽宽的土地、阔阔的空气。有民房一二、有劳作村民三五,在山间,似同无。如果稍微把目光往外撤,以一只无人机的视角看尹山,这一片地形更像一个巨浪的凝固。我们行走在这巨浪的钩弯处,到了严章红的门口,那巨浪形状更像。在他房子的西边,连浪的回头钩都清晰可辩。那便是一座小山构成了两种气象,钩外是万丈悬崖,钩内它护一大片平地。严章红在杭州做生意的儿子,接上话说,这就是金牛形,因前面是悬崖,金牛跌下去了,本来这块空间更大更宽。他的话很有意味,把地理形态与传说、与愿望、与想象揉合在一起,成为特别的解读角度、方法。其实小章这样说并非完全是无理的想象,严章红补充说:在那个山顶有一个巨大的坪,我们叫它野猪坪。
在这海拔560多米的空间里的这些旱地,是他们祖先躲到这里来的前提与理由。悠然如仙,淡然入画,自得其乐。
同样能够入画,同样是回头看山,你要是从里往外走在程家源村口一公里处,回眸一望,看到的天高尖气度非凡。我从自己拍的照片中看到了这样的气象:低近处是矮矮的山,画面的中间处是远远的天高尖。
天高尖在远方耸立,它的左边是比山尖低几十米的绵亘山岗,它的右边是一个大约成50度的笔直斜线,这线条一直到画面之外。整幅画面与前景的左右空间构成了这样一幅画:它既有层次感,又有无限感,还有空间感,最为关键的是画面干净又不断章取义。
副镇长胡国峰告诉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这座山还是与台湾斗争的演习场。冲上山顶一个来回要花大半天。
与“回头看天高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在桐坑源看桐岭。2019年9月1日下午三时许,我们在小雨中走进了桐坑源。在桐坑源的上村头往里看,在朦胧中极目远眺,远处的桐岭依稀可辩,桐岭山脉在这个角度看过去就是一个高高的山尖,成金字塔形。特别让人感到奇怪又很有型的是桐岭与前景组成的三重山脉形状的相反布置,桐岭是山尖、中间层是山凹,前景又是山尖,且依次降低,所以看起来很有画面感又形状别致。像这样的山形成的形状一定能入画。
梓桐山水入画来。它欢迎画画的,画画的岂止是欢迎这些山?
在梓桐这个小镇的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门面都装饰得很艺术、很古典的作派,字也是书法作品。在这些众多的店面里,有两家书画院,一家艺术馆。像这样一个农村小镇,有三家书画艺术院是不多见的。我在此下榻了两个晚上,住在一个叫“木辛舍”的民宿,这个名称很有特点,其实就是“梓舍”的意思,“梓舍”既是梓桐的家舍,也是故乡,故乡就是家。与“木辛舍”民宿一墙之隔的是“府前书画院”。2019年9月2号,一早醒来,推开窗门,看到户外有下过微微小雨的潮湿感与细雾感。抬头远眺,那一堵“富石山脉”映入眼帘。
眼帘中的山脉不同以往,因为有那么一些不薄也不厚的雾凝固其间,刚刚填掉了部分山岙,刚刚围上了部分山体。那一排山便完全成为了仙境粉饰,人间升华。那种展开就如同打开一幅长长的天宫图。一个个山尖或者说山岗,在贴上的效果里变成了隐隐约约的非人间世界。加上山脚下的田野,这种唯梓桐独有的仙鹤之气,多么珍贵。我个人觉得,“雾抚富石山脉”完全可以成为写生的一景。
在这个山脉的中段有一截有三个山峰,在黄村人眼里就叫三峰。在黄村人的祖谱里,把自己居住的这个地方,就叫三峰黄氏。我在老祠堂遗址的旁边,看到一幢马上要倒下的房子的门楣上写着“三峰小店”的字样。这三座小峰是“富石山脉”给黄村及黄村人的印堂,是乡愁的拐仗,是记忆不会沉沦的扶手。三峰是对面三座小山,如贴在山脉上的峰。在三峰之后,有一座处在界首洋田村的山峰,伸出脑袋露出山尖,在黄村的村前刚刚能够看到。黄国友说这是一座贼山,觊觎着黄村的财富与风情。这个说法很特别,把山说成贼山很少有,当然也很风趣幽默。被觊觎是因为有价值,有风景。连山也不禁伸出头来,偷偷地看看梓桐的乾坤。
不就是这如画、可画、成画的景致与风情吗?这一偷看便让山成“贼山”,便有了不一样的风情。
|
|
 浙江省公安备案 浙ICP备11047047号-2
浙江省公安备案 浙ICP备11047047号-2